文章关键词: 自杀奉献型人格人生体验抑郁

文章关键词: 自杀奉献型人格人生体验抑郁

晨光点亮波罗的海,蓝色地平线重新浮现群岛的轮廓。一艘轮船行驶在海面上,船身激荡出悠长白沫,转瞬又被吞没。24岁的王食欲站在船舱内,决定跳海自杀。
那是2019年夏天,王食欲在英国留学,确诊躁郁症,每天走在泰晤士河岸边,都有往下跳的冲动。为了实行自杀计划,她专门从伦敦飞往爱沙尼亚,又坐船到赫尔辛基,抵达公海,想免去父母为她跨国收尸的麻烦。
登船前一晚,她记录好银行卡和保险信息,给远在中国的母亲永爱打了最后一通电话。
电话铃声响起时,六千多公里外的中国天色已经擦黑。永爱记得女儿在电话里说,“生活没意思”,“不想活了”。相隔六千多公里,女儿的绝望从听筒中穿透过来,永爱从来没有这样害怕。她急着劝女儿,家里还有两只你养的鸟,如果你走了,它们怎么办?
过去的二十多年,女儿一直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初中成绩稳居年级前五,高中顺利考进名校,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大学期间,她创业开公司,独立买车,还担任过多档选秀节目的中插广告创意总监。
永爱不清楚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她猜测,当时国内影视业寒冬,女儿受到打击,也可能是人在异国他乡,学业压力也不小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女儿“太好强了”。作为母亲,永爱觉得自己脱不开责任。她说,这是“鸡娃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结果”。
鸡娃,是时下的网络用词,指父母用打鸡血的方式进行教育,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培训班,让他们奋力拼搏,停不下来。
这个词汇尚未流行时,永爱就已经是个标准的“鸡妈”了。她给女儿设定好完美的人生模版:清华北大,朝九晚五,自食其力,“最好是大学教授”。
女儿三岁半开始,她就开始不停报班,古筝、素描、乐理、芭蕾、工笔水墨、跆拳道、华数奥数……几乎填满所有假期。就算大学时去国外做交换生,她也要求女儿别忘了写书,记录经历。
虽然女儿后来的人生轨迹偏离永爱的设想,但早期的教育已经烙下痕迹,“她老想出人头地”,“做不出什么事就很懊恼”,永爱说。
王食欲确实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她每天花10多个小时写作,偶尔沉迷小说或者频繁刷豆瓣几天,就会不安,质疑自己浪费时间;接到任务,她习惯先设定目标,要求结果比目标至少好上20%。“我要求很低了”,对比曾经的同学,她说,“别人可是要翻倍的”。
母亲的教育让她容易“过度焦虑”。在王食欲看来,解决焦虑的方式只有一个,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,“做好就没有压力,有压力就是因为做不好。”
“她已经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了。”永爱叹了口气。这股自律和勤奋,曾让她引以为傲。
2019年夏天的那通电话,让她开始反思对女儿的教育。“鸡娃到一定程度,孩子没了,你何苦呢?”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笼罩在可能失去女儿的不安和恐惧中,整夜整夜失眠。
即便如此,永爱也不认为鸡娃这条路走错了,唯一的遗憾是,“把娃鸡到一个不能平凡的状态”。
两年后,我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永爱。她留着齐耳的短发,发梢末端微微卷起,一副金丝方框眼镜,看起来干练精明。
她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虎妈。女儿小学时跟同学打架,她平静地到学校领人,没有一句责备;有一次,她干脆从课堂上接走女儿,连家都没回,两人直接跑到内蒙古草原骑马。母女俩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,只有碰触到升学的事情,母亲权威的一面才会显露出。
回想起女儿降临、母女俩在手术室第一次脸颊相贴的时刻,永爱的眼眶湿润了。1995年夏秋之交,王食欲出生了,婴儿初生的那声啼哭,激起永爱心中最原始的母爱,“心一下碎了”。
年轻母亲有了欲望,“我的孩子得优秀”,“不能太差”。她说,这是一种做母亲的天然本能,“生娃而不‘鸡娃’,是最糟糕的家长。”
可王食欲开窍晚,学汉字拼命,po怎么都拼不出来;数数的时候,从0数到9, 就剩一双眼睛干瞪着永爱,怎么也不知道要接上10。
永爱纳闷了,“我怎么生了一个傻孩子?”
好在这是不轻易向命运屈服的永爱。1960年代,永爱出生在山西晋中一个普通的县城,母亲从小就告诫家里唯一的女儿,要靠读书改变命运,否则只能依附别人。永爱的母亲不惜借款供她读完大学。她成为那个年代的“小镇做题家”,毕业后,她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女儿出生后,为了维持家庭开支,永爱又离开体制,投身房地产行业。适逢房地产行业处于黄金期,她每年都能有不错的收入。
如今,永爱拥有几套房产,工作朝九晚五,再过两年要退休了。她的哥哥和弟弟,早年辍学,如今都在老家县城做电焊工。
时代的红利下,永爱相信自己能改变许多事。她30多岁还能从零开始,考取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,女儿肯定也可以。在她的经验里,六年级以前是鸡娃的最好阶段,因为“娃听话”,“能鸡得动”。她给王食欲讲数字规律,为了让女儿记住公式,学鸡叫和兔子跑,拿筷子在客厅里演练两辆火车的相遇问题。着急的时候,她还会直接一脚踹过去。
一次数学小测验,王食欲考了83分,听说很多人得了100分,永爱脸色变了,“怎么考这么低?”
她发现,那之后,女儿明白了成绩的重要性:考高分妈妈会开心,考低分妈妈不开心。只要自己不高兴,女儿就会顺从自己的心意,认真学习练琴,“宁愿虐自己”。
陷进回忆,永爱又掉泪了。她满怀愧疚,可她说,“鸡她,也是因为爱她。”很多年后,她才得知,女儿当时“只觉得她对我不好,不爱我”。
过往经历奠定永爱实用主义的底色,“没什么用”,经常被她挂在嘴边。小时候,女儿下楼找伙伴玩,永爱说,“没什么用,浪费时间”。素描、国画、手工科技课是女儿喜欢的,但都被永爱取消了,因为“没什么用”,“钱扔进去也听不着响”。丈夫带女儿到宋庄买画,她告诉王食欲,“这些画家都吃不上饭,没暖气,你不要搞这个。”
成绩和升学是她心中的唯一标准。她给女儿报了一年的800米长跑和立定跳远,就为了中考体育拿满分;古筝也学了10多年,因为考级和特长加分,授课老师建议走专业路线,永爱拒绝了,艺术不能当饭吃,她只要眼前的加分。
不是没有心软过。从少年宫下课回来的路上,年幼的王食欲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昏昏欲睡,永爱一手往后稳住女儿,一手扶住自行车把手。她心酸,觉得“孩子不容易”。但要克服心中的软弱——这是为女儿好,不能让女儿以后埋怨她。
那是永爱最忙碌的人生阶段。丈夫是个文艺青年,做媒体工作,经常上夜班,连续几天没回家,一问才发现去四川出差了。家里的活只能撒手给永爱。她还要忙着送礼、送钱,给女儿争取一个在剧院演出古筝的机会,为小升初的简历加上一笔。这样的简历她亲自排版,装帧成册,印了50多份,全市最好的一批小学,她挨个投遍。
永爱说自己是奉献型人格,她有一半工资都用来给女儿报班。她的奉献也的确获得了回报:小学六年级时,王食欲成绩已经保持班级前三。初中三年,王食欲每天放学主动写作业,自己搜寻辅导班,成绩稳坐年级前五。
永爱成为家长们的典范。每次家长会前,她都精心打扮一番,等待被邀请上讲台,掏出事先拟好的演讲稿。
女儿就是她的另一项事业。
2010年,鸡娃的第13年,经过四轮面试,王食欲成为一所知名高中的学生。永爱终于松了一口气,“离北京大学就是踹一脚的事了。”
残酷的现实随着高中大门的敞开迎头撞来。18个同学坐在一间教室,穿同样的校服,天差地别。有人捧着美国物理教科书学习,全英版;有人英语SAT满分,又自学拉丁文;有人已经在跟中科院院士做实验。
而王食欲,数学测验,一张A4纸,5道题,曾经自诩数学优异,现在一道也解不出。同学说了句,老师都讲得这么明白了,还不懂?
“为什么我的同学都这么优秀?”她试图延续从前的方式:“只要鸡自己,总能赶上同学。” 毕竟这是她和母亲实验过的,最有效的方法。
小升初时为了拼个好学校,她曾经连续两年的周末,都花在辅导班,但最终没能进到心仪的学校。
她当时就明白了一件事,有的人靠父母,有的人靠实力,而她是父母和实力都没有,唯有“自鸡”。
每天早上在永爱的汽车里,王食欲开始背诵英语。放学后,她用坐地铁和公交车的时间,写课内作业,没座位的时候,她就打开MP3练习英语听力。一到家,她开始写课外辅导班的作业,几乎没有在11点前睡过觉。
初中三年,她不仅成绩靠前,还当班长、学习委员、团支书,给老师改作业,期末大扫除跟着老师干活,“可狗腿了”。
在王食欲的印象里,母亲永爱“已经基本不太行了”,遇到不懂的题,问了也是一脸茫然。母亲的参与从引领变为支持,王食欲一提要上辅导班,永爱就搜寻资料给她做参考,或者干脆按照指示交钱。
升学的焦虑就像一个幽灵,游荡于每个角落。同班的一个女生,头发掉得厉害,十几岁就斑秃;考试差两分第一名,趴在书桌上大哭,因为回家会被打;为了不让同学做同一套题,她甚至撕掉别人的练习册。同学关系不冷不热,每天只有无限的习题和辅导班,王食欲有时候觉得,生活没多大意思了,“只能忍着”。
沉闷的生活里,写作是唯一让她感到享受的事。最快乐的时光是,初中和同学在路边,指着一棵树一朵花做故事创作和接龙。在中学拥挤的公交车上,她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心中的小说。每天时间都被功课占满,只有睡前半个小时能用来写作。后来她给杂志投稿,文章还被录用了。
韩寒郭敬明大火的年代,王食欲决定休学全职写作。永爱不同意。王食欲用行动抗议,不写作业,不上辅导班, “想让我妈重视起来”。僵持几个月,母亲反应平淡。王食欲只好重新回到升学的壳子中。
从来都是这样。小时候,她想学做火箭、改装四驱车,也想学画画,永爱不同意,依旧是语数外辅导班轰炸课余时间。后来,她就变得无所谓了,“随便了,反正选择也不在我”。
她说,自己妥协了。连她也觉得生活的目标就是 ,“上一个好学校”。
现在,她的目标实现了。可现实的裂缝再一次在眼前缓缓打开。10万元的南极游学项目,午休时间,50个名额被一抢而空。在地理课本上第一次看到东非大裂谷时,她的同学早已经亲临现场。高考和成绩是她生活的全部,而对别人来说那就像一种顺带的人生体验。
曾经的优秀、骄傲,在高中的漩涡里化成一粒沙,消失不见。更重要的是,她发现,再怎么“鸡”自己都没用了。
那时候,在别人的影响下,王食欲已经开始吃素和研读佛法,《心经》里一句“心无挂碍,无有恐怖”,让她印象深刻。后来,她反过来劝永爱,“妈妈,《金刚经》说了: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我这次没考到平均分,咱不能往心里去。”
可还是不甘心,有时候她也会回家“鸡”母亲,“你要是XXX(一个同学)的父母就好了。”
永爱的实用主义在高中校园里也瓦解了。王食欲所在实验班不以成绩为导向,班里一半以上同学都有出国计划,启发和培育学生的都是那些在永爱看来“听不着响”的兴趣。
那三年里,实验班请剑桥讲师来讲《批判性思维》,请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导演薛璐晓给他们讲电影和纪录片。历史课上大家探讨竹林七贤,课后还能参加国学社,戏剧社,爱心社等活动。王食欲的同学里,有人搞摇滚,有人停课骑行去西藏,还有人因体型高大、上不去国内的公交车,转而研究新型公交车设计。还有一群人,在“模拟联合国”里,探讨如何解决非洲饥荒、美国枪支管理、印度种姓制度等世界问题。
所有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,成绩在这里不是唯一重要的事。
经过最初的失落后,王食欲发现,只要找对自己的位置,就能活得很好。
有一次,生物课上老师解剖青蛙,讲解构造知识。王食欲冲到实验室质问老师:“为什么非得解剖才能讲?你这是在杀生。”一战成名。同学都在讨论王食欲的独特与勇敢,这让她受到鼓舞。“你知道那种感觉,就不会太在乎学习了。”
写作、拍电影给她更大的存在感。高中期间,她花几个月,到五个省拍摄尘肺病纪录片,获得国际大学生电影节奖,学校家长还因此给尘肺病人捐款5万。王食欲沉醉在那个世界里,她在学校也变得受欢迎,新年晚会上,好几个男生邀请她跳舞。
女儿变了,放学后不再自觉地趴在课桌上学习,成日捣腾写作、拍摄的事。永爱急了,“这一天天不学习,考不进北大可怎么弄?”
人生突然变轨。这一次王食欲决定自己掌握方向盘,终点不是清华与北大,而是北京电影学院。
永爱的世界坍塌了:“鸡了这么半天,就上这么一所‘烂学校’?”在她眼里,那就是一所文化课成绩极低的“技校”。北大才是永爱的完美梦想。当年小学同班女生考上北大,永爱的母亲总说,“你看谁谁谁,人家就能考北大。”
她和王食欲吵过,也劝过,“咱们进名校,不就是要考清华北大,将来好就业吗?”
王食欲没当一回事。初中她私下写作,小说和文章被杂志刊发,成为进名校自主招生的敲门砖,那时候起,她就发现自己的选择也可以是正确的,“之后,我就不会再听我妈的。”
永爱后悔了,后悔把女儿“鸡”进了名校。和女儿逐渐找到自我相比,这三年她始终被焦虑折磨。名校的家长,有人是人大代表,有人拥有一条街的商铺,还有人是大学教授。她只是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员,和他们相比,家庭条件只能算中下。当别的同学去南极时,她只能负担女儿去美国做交换生——那是整个寒假所有游学项目中,最便宜的一个。
版权声明: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,另有声明除外。
 推荐课程
推荐课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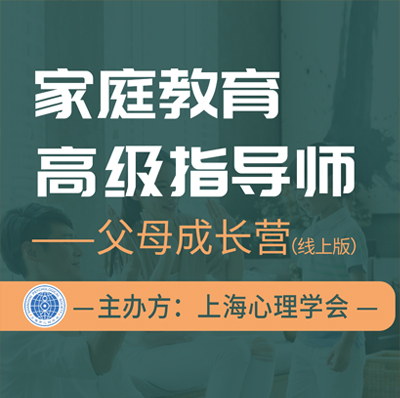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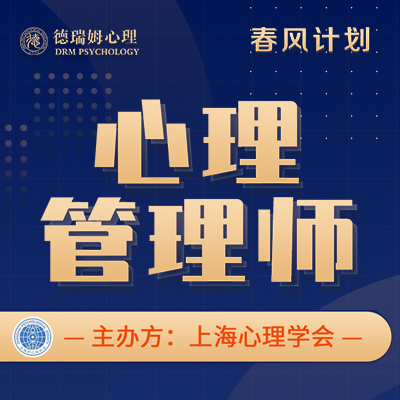

 热文推荐
热文推荐